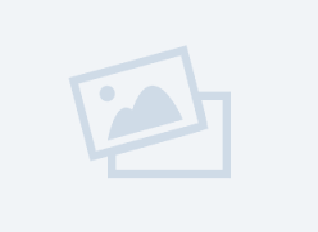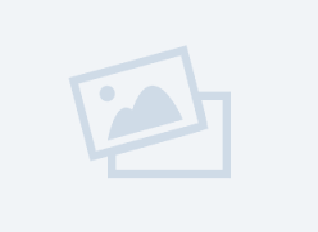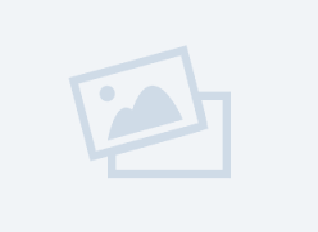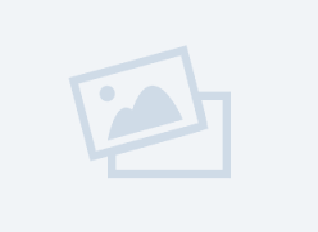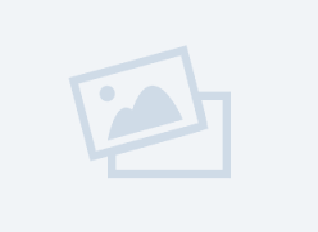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,心中萌生了做医生的梦想。只记得小时候,有一次两个小孩溺水,大家手忙脚乱地把孩子们拖上岸,却不知如何施救。直到医生赶来,众人才松了一口气。那一刻,人们满怀希望地看着医生的眼神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穿着白大褂的医生,在我心目中显得格外伟大而神秘。或许从那时起,治病救人就成了我梦想的职业。
高中时,我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,毕业时年仅15岁,填报志愿全凭老师和父母的安排。最终,我被师范学院录取。读了一年多后,我心中对医学依然有强烈的渴望,于是决定重新参加高考,希望能考上医学院。然而,命运再次捉弄了我:老师擅自在我的志愿表上加上了“服从安排”的选项,结果我被农业大学录取。拿到通知书后,我并不甘心,但在父亲和他那些农业大学毕业、如今在县城任职的同学朋友的劝说下,我最终还是扛不住压力,前往农业大学报到。
尽管我争取到了第二次高考的机会,命运却似乎不肯让我踏入医学院的大门。
当医生的梦想看似不可能了,但它始终深藏在我心底。
有一天,我从农业大学沿着山路散步,经过泰山医学院门口,又在医学院旁的冯玉祥墓前练了一会儿武术。突然,一个念头闪过:如果能转到泰山医学院上学,既能实现当医生的梦想,又能在这片地方练武,岂不是两全其美?然而,在80年代初期,从一个大学转到另一个大学,尤其是跨专业转学,简直是闻所未闻。当时,农大曾有一名学生因试图从畜牧专业转到园林专业,被学校以“不热爱本专业”为由开除。
貌似不可能的事,但是不试怎能甘心?我天性敢想敢干,想到就要去做。
于是,我开始四处奔走:去两所学校的教授和领导那里游说,去省教委争取支持,甚至回到老家枣庄市教育局寻求帮助。幸运的是,父亲没有责备我“瞎折腾”,反而帮我四处奔波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最终我成功获得了转学许可。唯一的条件是,我需要先跟着83级学生上一个学期,等到84级学生入学时,再与他们一起完成学业。这意味着我要多花一年时间,再加上医学院本身就是五年学制,我将比原来的大学同学晚两年毕业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终于,我踏上了实现梦想的道路。刚到医学院报到,我就迫不及待地穿上白大褂,在校门口拍了一张照片,心中充满自豪。后来,去医院见习时,我甚至在回校的路上也舍不得脱下白大褂,仿佛要用这身装束向世界宣告:我是一名医生。
从进入第一所大学到医学院毕业,我整整花了八年!别人八年都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,而我才刚刚完成本科,拿到一个学士学位。
然而,我从未后悔,反而很庆幸自己终于踏上了从医的道路。
1989年,医学院毕业的那一年,我又萌生了一个更大的梦想: 去医学最发达的美国,成为世界一流的医生。怀揣着这份憧憬,我历经波折,自费来到美国。然而,那时的我对如何在美国成为医生一无所知,甚至连考USMLE这条路都不知道。我曾向人倾诉自己的理想,却被告知这是不可能的。爷爷更是直言不讳地泼了一盆冷水:“你痴心妄想!在美国上医学院的,都是最聪明的美国学生,而且家里要有钱。你有什么?”
是啊,我确实什么都没有——不聪明、没钱,还有语言障碍。
当医生的梦想,再次变得遥不可及。
那时,计算机专业被认为是一条短平快的路。通常只需两年就能拿到硕士学位,而且就业前景很好。我叔叔正好是计算机系教授,还能给予我很多帮助。在亲戚们的建议下,我决定暂时放下医学梦,先转读计算机,希望先尽快实现经济独立,再谋后路。
我的数学基础好,又有叔叔和他的博士研究生们随时指点,因此学习计算机相当轻松,成绩一直名列前茅,未来的职业发展也十分光明。与此同时,刚到美国一个月,我便开始教授武术。起初是在芝加哥市区的武馆任教,后来自己在郊区开办武馆,生意蒸蒸日上。凭借计算机工作和武馆收入,按部就班,短短几年我便可以实现经济独立。
按理说,这是一条轻松而且稳妥的道路。然而,我的内心却始终无法感到真正的快乐。因为我来到美国的初衷,不是为了过上安稳的生活,而是要成为一名医生,而且是一流的医生。
眼下这条路虽然顺遂,却与我的梦想渐行渐远。
于是,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:放弃再读一年就能拿到的计算机硕士学位,放弃自己辛辛苦苦闯下的蒸蒸日上的武馆,毅然前往达特茅斯大学(Dartmouth)攻读药理学博士。尽管药理学博士与成为医生仍相隔甚远,但相比计算机专业,毕竟更接近医学这条道路。
在博士学业稳定后,我开始着手备考美国医生执照考试(USMLE),通过考试后便可直接申请住院医生职位。当时恰逢达特茅斯医学院新开设了一个MD/PhD双博士学位项目,我意识到,若能拿到达特茅斯的医学博士(MD)和哲学博士(PhD)学位,不仅能进入更好的医院接受培训,也更有机会选择自己心仪的专业,实现成为一流医生的梦想。
然而,这种双博连读项目竞争极为激烈,录取要求异常严苛,基本上只招收最优秀的美国学生。达特茅斯医学院每年仅录取1-2人,而我,一个国际学生,几乎毫无胜算。这个目标,对我而言,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
但我始终坚信,凡事只要想到了,就应该去放手一搏。
于是,我鼓起勇气,直接去找了当时达特茅斯医学院的院长: Dean Andrew Wallace。是的,他的名字,至今刻在我的脑海中。面对这位医学院掌舵人,我毫无保留地阐述了自己的想法:为什么我要加入这个项目?为什么我要再上一遍医学院?我希望将东西方医学理念相融合,把基础医学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,让临床为基础医学指引方向,让基础医学推动临床发展。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加全面、更加优秀,成为最好的医生。
我的执着和理念,最终打动了院长。他认可了我的想法,也认为我完全有资格进入这个项目。就这样,我成功获得了录取资格,踏上了这条更加艰辛却也更接近梦想的道路。
又是整整八年,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了下来,最终拿到了MD和PhD双博士学位,终于成为了一名美国执业医生。
医学院毕业时,Dean Wallace和当时的内科系主任都鼓励我不要留在本院,而是去更广阔的世界施展抱负。内科系主任更是充满信心地鼓励我:“你以后一定会进入全美前五的顶级医院工作。”
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,我终于感受到,那个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,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。
后来,我在克利夫兰诊所(Cleveland Clinic)完成住院医培训,在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(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) 完成肿瘤内科专科训练,随后在休斯顿MD安德森癌症中心(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) 担任专科医生和助理教授,并领导“消化道肿瘤免疫疗法实验室”。
这些医院,都是世界顶级的医学殿堂。在这条路上,我一步一步,接受了最顶尖的训练,最终成为了一名一流的肿瘤专科医生,实现了我一生的梦想。
回首这一路,从一个鲁南山村穷孩子到一流的美国执业医生,我到底付出了多少?
在国内,我辗转三所大学8年才拿到医学学士学位;在美国,我又用了整整 15年,拿到了 MD/PhD 双博士学位,并完成住院医及专科医生训练。为了这个梦想,我足足付出了 23年的青春年华。
23年,值得吗?
人生能有多少个23年?如此不惜一切代价去追逐梦想,是不是太固执?或许是的,但我从未后悔。
年轻时,我曾总结自己的性格:“做梦且追梦,求缘但随缘。” 如今回望,这对我依然是个精准的描述。